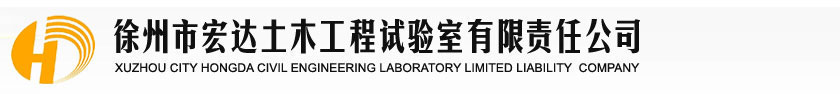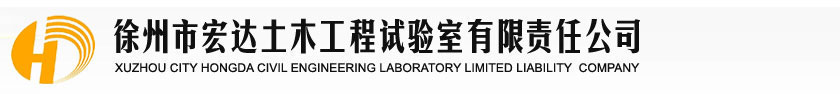假期,因着女儿正在背诵的一篇《赠汪伦》,带着女儿走进了踏寻桃花潭的旅程。
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心中不由畅想:桃花潭,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去处。
踏进深幽的古巷,置身于淡淡的青烟之中,漫步在碎石铺就的小道上,轻抚着长着青苔的砖墙,间或一只小猫从身前穿过,“刺溜”一下,消失在颓圮的篱墙后。
我骤然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,朦胧间,仿佛看到李白在这里醉卧,陆游在此处惆怅,戴望舒撑着油纸伞,牵着丁香一样的姑娘,轻轻向我走来。我心头一凛,一切便又烟消云散,只剩下闲坐的老人,在半掩的柴扉前微合双目,兀自假寐。他似乎要告诉我,千百年来,时间早已在这里凝滞,与李白把酒,同陆游对诗,不过是他脑海深处一抹青涩的回忆,身前身后的一切,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云烟。
我静静地走过去,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,生怕惊扰了历史。
古巷的尽头,是一座小楼,下面是一条甬道,不知通往何处,上面是一间小阁,白墙灰瓦,交藤荒蔓,古朴地极有韵味。忍不住循着逼仄的阶梯登了上去,在仅容回转的小阁间匆匆环视。此间光线幽暗,四周悬挂着文人墨宝,黄卷青灯,倘若静下心来,这里倒是读透人生的上佳之处。
穿过甬道,眼前豁然开朗,清澈的青弋江微波粼粼,从流飘荡,任意回转,在此间形成一处深潭。这,便是桃花潭了。只见潭面水光潋艳,碧波涵空,潭岸怪石耸立,青藤纷披,一叶偏舟缓缓悠悠地飘荡在水面上,乘舟而行,耳边传来潺潺水声,啾啾莺啼,恰如淳朴好客的乡民踏歌而行,向远方的来客表达厚谊热忱。
夕阳斜照这幽幽的古巷,阳光从缝隙中挤进来,告诉我,这静谧的古巷,蕴藏着一个又一个秘密。我无意去揭开回忆的厚幕,窥视远去的史乘,只求在斑驳的墙壁上读取先人的杂记。
我漫步在青石小路上,遥想当年,好客的汪伦为了邀请诗仙莅临,编织出善意的谎言:先生好游乎?此地有十里桃花;先生好酒乎?这里有万家酒店。李白闻之,欣然而来,与主人把酒言欢。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,敦厚的乡民又怎好欺瞒豪情的游侠,眼花耳热之后,汪伦便据实以告:桃花者,实为潭名:万家者,乃店主姓万。诗仙闻言大笑不止,并不以为忤,反而被汪伦盛情所感,在此驻留十余日,临行之时,汪伦又馈以厚赠,更率领全体乡民载酒踏歌,留下千古佳话。
我不由地产生强烈的愿望,要与这好客的主人一会。
一代诗仙长眠于采石矶畔,不知九泉之下,可有纪叟的老春佳酿,可有汪豪的万家狂药。纪叟的酒肆早已不知踪迹,万家的旗幌却依旧迎风鼓荡,只是在这陋巷之中,鲜有来客一品清酌,即便有人前来附庸风雅,却再也不复当年之诗情豪意。剩下的,只有单调、沧桑和沦落。
不知不觉,古巷中迷雾轻飞,一切都渐渐地朦胧起来,我信步游走,忽地,竟踏进一座小园。小园早已荒废,枯柳斜舞,灌木寞寞,一番萧索景象,心里一颤,忆起桃花潭畔碧桃遍地,花海起伏,蜂飞蝶舞,雀鸣莺啼。 相隔咫尺,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幅景象。再抬头看去,只见荒园正中却是一座孤冢,这便是汪伦墓了!
谁曾想,南阳古镇的豪士,身后竟如此地寂寥,那豪迈的辞令,欢快的乐舞,以及深厚的情谊,难道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了吗?
徘徊在纠缠的苦念里,动不了脚步,此际荒园孤影,寂寥光景,茫然得心慌,杂念奔突,却怎么也奔不出一片开阔天地。
暮光渐隐,天地无人。
然而,我毕竟释然了。
其实,说起桃花潭,在江南并不算得如何出奇,青弋江在旁人眼中,也不过是一条宁静的长河,若是匆匆走过,绝然不会将之挂在心上。
然而,这一切却使我们魂牵梦绕。
倘若仅仅从诗歌的意境和美学的角度出发,李白笔下的桃花潭诗章称不上上品。然而,当李白被玄宗礼貌地逐出京城时,人生最大的梦想也随之破灭,一个落魄的才子,仗剑载酒,行走江湖,看似潇洒风流,却不知欢笑的背后有多少的无奈和酸楚。茕茕孑立,形单影只,正当他的灵魂无所寄托时,却在这里寻求到了归宿,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年,并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情谊。《赠汪伦》,与其说是诗,不如说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暮年老人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。打动我们的,不是这里的美景,而是这里的深情。
桃花潭接纳了李白,李白成就了桃花潭。
当黄昏的余华消尽,桃花潭流溢着温馨的色调,古巷在渐渐溢满的苍茫中结束一天,朝为夕露,暮作沉寂。
李白流淌不止的诗行从青石上滑落,化作今日的静谧,它就这样静默着,悠悠地弹奏它的色调。一千多年亘古不变,化作秋浦白发的臆想,如同一位邈远天地情的老者,笑着看着人们生长,老去,生生不息……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