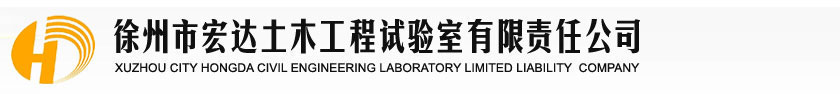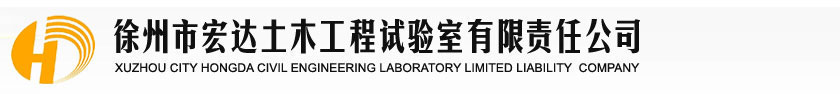暗房红灯闪烁,一张底片在显影液中缓缓浮现。堆积如山的尸体、被刺刀挑起的婴儿、冒着浓烟的街巷——当这些画面在这间照相馆里,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城里,成了人性与历史的显影池。
邮差阿昌为保命冒充照相馆学徒,被日军摄影师伊藤押解着推开吉祥照相馆大门时,他不知道自己踏进的是历史的暗房。当他被迫冲洗日军“亲善照片”时,显影盘里浮现的却是地狱景象:巷口卖糖画的老人倒在血泊中,邻家女孩蜷缩墙角眼神空洞,而更令人窒息的是日军为拍摄“和谐画面”当众摔死啼哭婴儿,又令林毓秀抱着死婴强颜欢笑的场景。这些画面在暗房红灯下如血浪翻涌,照相馆众人从底片上第一次看清了南京城的真相——这不是战争,而是屠杀。橱窗之内,照片曾仅被视作历史冰冷的证物。电影中,日军士兵一张照片被单独放大展示,那僵硬的手指与军服领口歪斜的纽扣,仿佛无声诉说着战争机器的可怖。照片背后,是无数冰冷而庞大的数字——三十万同胞如尘埃般被吹散,飘落于历史的深渊。在电影放映厅的昏暗中,我凝视着那些照片,它们似乎正默默承受着历史无法承受之重。历史无情地碾过,常把血肉之躯压成单薄数字,当数字成为历史的单位时,人性就消失了。
每张照片都在等人认领,只是不知何时才被认出。所谓历史证物,其内里蕴藏的,原来是一张张曾经鲜活的脸庞,一缕缕等待被辨认的灵魂。相纸所承载的,不仅是凝固的瞬间,更是人间苦难等待被接住的信物。
片尾,秦淮河的血水化作今日梧桐成荫的街道。当真实的历史罪证照片叠印在现代南京的街景上,“显影终将发生”的字幕浮现。这便是15岁学徒罗瑾的真实故事——他冒死加印的日军暴行照片,经吴旋藏于佛像腹中六年,最终成为审判战犯的“京字第一号证据”。正如申奥导演所言:“电影会比所有主创活得长久”,这些显影的底片,正是刺穿历史谎言的匕首。
走出影院,车水马龙声复又灌入耳中。橱窗内外,照片与行人依旧隔着玻璃彼此凝望。我恍然明白,照相馆岂止是照相馆,它分明是一间贮存着无数未寄信件的邮局;照片也岂止是照片,它们是那些未能发出的信笺,信纸上泪迹未干,在历史的风中静候着被拆启的时分。
当历史化作数字,照片便成了唯一能证明“我”存在过的凭据。橱窗里那些悬停的影像,不只是等待被认领的脸庞;那是历史深处无数双眼睛——它们注视着当下,正等待我们以灼热的同理心,赋予那些无名以名字,让死寂的数字重获体温。
|